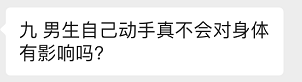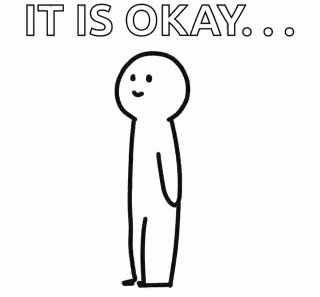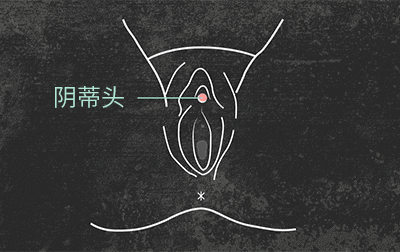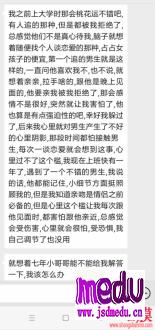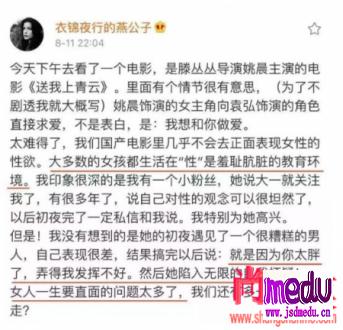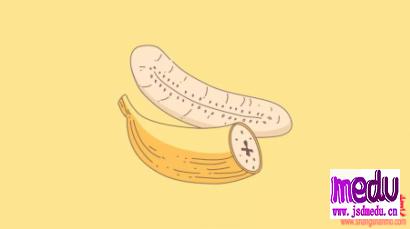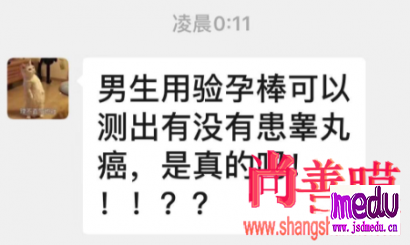想说一些
关于
N号房事件

写在前面
今天是韩国N号房事件在中国引起舆论关注的第八天,这个事件和曾经所有的热搜一样来去如风。
在很多人都即将遗忘的时候,国内版“N号房”事件被爆出,又激起了不小的浪花。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它也会在信息洪流中落幕。
但作为写作者,记录本身,即是反抗。
于是Ann联合Shelly打算就此事件开展专题写作。
今天的文章是专题的第一篇同时这篇文章也会同步发在我和她参与运营的medu网站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

何为N号房事件?
N号房事件指近期在韩国发酵的一起数码性犯罪事件。运营者(嫌犯)在通讯软件Telegram建立多个秘密聊天室,通过非正常手段诱骗或胁迫女性(包括未成年人)拍摄色情影像,并在收费的虚拟房间内共享这些网络聊天室和我们的聊天群相似,在韩国被称为“房”,运营者将非法制作或获得的淫秽影像放到多个不同的收费“房间(聊天室)”,因此被称为“N号房”。
据悉,涉案通讯软件上此类“房间”超过60个,参与人员高达26万人,受害女性不计其数。
更让人震惊的是,受害女性中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
几十名女学生在这段时间受尽虐待,被迫拍摄用刀在腿上刻字、针穿乳头、以刀或剪刀等危险物品自慰、乱伦等影像,或被带到大街上被路人抚摸胸部。
聊天室里不仅充斥着这些影像,少女的姓名、就读的学校和班级等个人资料都在其中流通。
嫌犯们威胁受害者,若试图抵抗,便会公开她此前拍摄的所有影像和个人信息。

为什么N号房事件会发生?
N号房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全球性的震惊与抵制,与其说是因为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色情影像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大众的反感,不如说是N号房背后的参与者的变态性心理让大众感到恶心和恐惧。
26万人围观以未成年女性为主角的性虐待、强奸影像,相当于在公共场所围观性犯罪,且无人制止。
N号房的性虐待和强奸影像不乏受众的背后,是26万人对感官刺激的趋之若鹜。
“房间”内一万余名高级会员的犯罪动机,不排除有通过逼迫女性摄录影像、利用影像泄露可能带来的身败名裂要挟女性,从而获得操控和欲望满足的快感的可能。
但就数量最多的、仅限于观看影像的普通会员们来说,不惜趟这趟浑水,大概是为了满足扭曲程度不等的性心理需求。
性虐待影像的制作动机,和身体敏感部位的偷拍影像的制作动机相似——被摄对象的恐惧和无法抵抗,将给施行者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快感。
腾讯微信中,和偷拍有关的medu网站比比皆是,但在N号房事件之后,一众大V带头呼吁网友进行举报和抵制。
在新浪微博中,有关偷拍的内容虽然已多被查禁,但在此前也是十分猖獗。

受这种扭曲性心理快感支配的N号房会员和平时的偷拍者,实质上是将性作为证明能力的工具和手段。
他们用性来获得认可与欢迎,把动物世界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人类社会里迷醉自我——而这一切的根源,是性羞耻心理在作祟。
不可否认的是,性羞耻存在于大多数人心中,对性讳莫如深是性羞耻心理的体现;讲欲盖弥彰的黄色笑话亦是性羞耻心理的体现。
性羞耻心理的衍生物,便是认为性可以被用来羞辱和伤害一个人。
施害者利用了受害者的性羞耻心理,对受害者进行侵犯;而受害者还要活在这种羞耻里,可能终其一生都走不出去。
国内长期以来对性的污名化,为性羞耻心理的诞生提供了温床。

为什么会出现对性的污名化和性羞耻?
李银河曾经这样描述过:“性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一个怪物。
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处不在。
”而这个现象的成因,还是要从我们本土的历史文化中去追寻。
当回溯《诗经》时,我们会发现,《诗经》中将性视为自然,宽容人的正常欲望,亦包容人对自由恋爱的渴望。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虽然西周也是一个包办买卖婚姻的年代,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崩塌带来的伦理的瓦解,人们其实对性更加包容。
李银河也曾这样描述过:“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中,中国人的性观念对性持有基本肯定的看法。
概括地说,中国的性规范强调以下两种观念:第一,阴阳相合;第二,节制欲望。
”李银河也尖锐地发问:“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并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社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为什么这个对性没有偏见的社会几乎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难道说性在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与古代中国不同的东西,从天地自然变成了洪水猛兽?”而我更倾向于阮芳赋的解释,他认为,中国人对性的态度在前4000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从1000年前(宋代,960年)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否定、压抑。
宋朝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女性开始被要求缠足,社会对女性的禁锢越来越多,存天理灭人欲开始提出,这也是一个逐渐扭曲的时代。
存天理灭人欲本是为了灭掉人身上不好的欲望,但是发展到后面,却提倡灭掉一切欲望。
这是拿圣贤的标准要求一个个普通人。
而朱熹本人实际上也绝非什么圣人,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如果大家去了解“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的诗词出处,会发现朱熹不过是一个为了打压异己可以冤枉无辜之人入狱的小人。
从这个逐渐走向过分集权的时代开始,女性的枷锁越来越重。
其中最鼓励的就是当丈夫死后,女子不改嫁,或者说最好殉情,可以拿到一块永久流传的“贞节牌坊”。
这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是一份无上的荣耀和纳税上的优待。
经过宋、元、明三代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在进入清朝以后,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了,似乎成了一种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
总之,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
清代的儒道学者们连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这是什么事!你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女子如果做几句“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也要被斥责为“邪念”、“怀春”。
清代时,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矗立大牌坊。
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中,春秋致祭。
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由本家为其建坊。
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
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
这一来,把对节妇烈女的崇尚推至极点,成千上万的妇女以身殉夫,或自愿、或被迫,此风愈演愈烈。
随之出现的女子教训书中,也增加了大量的宣扬贞节的内容。
如康熙、乾隆年间蓝鼎元的《女学》、陈宏谟的《教女遗规》、李晚芳著的《女学言行录》、王相的《女范捷录》等等,流传甚广。
也从明清八股取士开始,许多关于美的文艺作品被打入地狱。
《西厢记》等这些在我们看来流传千古的爱情经典在这个时候被贬为禁书、淫书。
对人的思想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便包括对人的性禁锢。
从宋开始,直至清朝,对人的性禁锢逐渐走向顶峰,对压迫禁锢女性的贞节观念基本上灌输完成。
——百度百科词条“贞节牌坊”(有删改)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多扭曲的贞节观念已逐渐消失,但仍有不少糟粕保留至今,发展到现在,逐渐发展成性羞耻观。
“他插进来,而我为此感到抱歉”这种房思琪式的性受害羞耻观就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女性千百年来被灌输的性羞耻感。
因此,各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受害者有罪论大行其道。
所以大家会看到,片面要求女性贞洁的观念并不陌生,尽管这是非常荒谬而又可笑的。
中国人经常讲究直觉和常识,而不讲究科学和逻辑。
而这种常识又是从离我们最近的朝代开始的,所以“女德班”大行其道并不意外。
而这种性压抑和性羞耻并不仅仅只是影响到了女性。
直至今日,我国法律中强奸罪一条针对的受害者仍然是女性。
如果男性被强奸,则不叫强奸,而是“强制猥亵”——人们通常不认为男性会被强奸。
尽管据BBC报道,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六分之一的男子是强奸或者是性虐待的受害者,每小时就有8名男子受到性侵犯。
在人们的这种认知偏差的情况下,男性受害者往往不敢声张。
他们只能比女性更加沉默。
性羞耻心理影响下的中国性教育刚刚在饭桌上,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
”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
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有开学。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至少就目前看来,中国的性教育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和发展。
但如何把握性教育的边界和尺度、如何让性教育在国内获得大范围的普及,依旧是难题。
专业的事情当然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在此就不班门弄斧了。
中国性学研究专家方刚认为,“现在中国的性教育还处于调情阶段:总说要做,但就是不做。
中国的学校性教育基本为零。
”方刚认为,好的性教育应该是赋权型的:性是自主、健康、责任。
校园内的性教育,还要依托教育者的推动。
但在校园之外,关于性,我们这些“非专业”的人起码可以先给自己和身边人进行一场性教育——做到拒绝性羞耻心理,为性去污名化。
去污名化的前提是正视,而不是回避。
性器官是人体的一部分,和眼鼻耳嘴一样拥有学名、也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不需要遮遮掩掩避之不及,更不需要用来开无聊的玩笑。
为性去污名化,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在谈到性的时候不脸红心跳。
污名化带来的是误解,而误解则会增加恶行和恐惧。
在体格和力量上占优势的优越感,不是用性来凌虐弱小者的理由;身体从来都不属于其他什么人,它只属于你自己,具有独立的价值。
我们应当有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偷窥的权利和勇气,也不必在经历一些苦痛后认为身体会受到污染、不再纯洁,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所有物,所有的污名化都不过是社会目光的凝视,而这本不应该对我们自己产生影响。
2018年7月5日,中国第一批性教育工作者得到国家部门颁发的证书,其中13人获得高级证书。
随着性教育的普及,性羞耻心理将会逐渐消失,但无疑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此之前,可以先从自我和家庭出发,逐渐克服“谈性色变”。
最后
N号房事件并不是女权主义者才去关注的问题,在这种严重的性剥削和性暴力之下,我们要对立的并不是性别,而是违法犯罪。
而在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受害者并不只有女性,也有男性。
只有当我们主动地去克服性羞耻,去除对性的污名化,从这个时代的枷锁中实现自我解放,才能够更好地对抗那些实施性暴力的罪犯,去遏止那些可能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性暴力事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那些曾深陷地狱的孩子,找到自我救赎的路径。
上一篇:做“羞羞的事”被儿子发现怎么办?
下一篇:男生的第一次有多久?